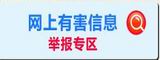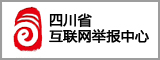校园里的泡桐花开了,粉白的如风铃一样的花朵随风飘散,落在心理咨询室的小窗台上。朱老师推开窗,一朵花恰好落在她手中的记录本上,她轻轻拂去,目光却停留在那一页——“高三(4)班李明,第三次咨询”。作为学校特聘的心理咨询师,朱老师对这个成绩优异却心理脆弱的李明同学印象深刻。
李明第一次来时,是班主任硬拉来的。那孩子缩在椅子上,像只受惊的鸟,眼神闪烁不定。他说自己睡不着觉,一闭眼就是考试倒计时的数字在眼前跳动。朱老师注意到他右手拇指的指甲已经被咬得露出了粉红的肉。
“我们可以试试呼吸法。”朱老师递给他一杯温水,“就像品茶一样,先闻一闻,再小口喝。”
李明接过水杯的手在发抖,水面上荡起细小的波纹。朱老师忽然想起十年前自己刚入职时的样子,面对第一个有自残倾向的学生,她的手抖得比李明还厉害。那时老校长对她说:“心理健康不是贴膏药,是搭桥梁。”
窗外的泡桐花被风吹得簌簌作响,将朱老师的思绪拉了回来。李明正在尝试深呼吸,胸口起伏得像浪花。第三次咨询结束时,他主动问:“老师,下周我还能来吗?”
四月的校园里,摸底考试刚结束。朱老师在食堂排队时,听见身后两个老师在议论:“现在学生太脆弱了,我们那会儿……”她转身微笑:“王老师,您最近睡眠怎么样?”王老师一愣,摸了摸自己浓重的黑眼圈,重重叹息一声,王老师才开口:“我女儿……抑郁症休学了……”他的声音哽咽得像要断流的小溪。
当天下午,教师休息室里多了一张海报——教师心理健康沙龙召集令。起初只有三两个人来,后来渐渐坐满了。数学组的李老师分享他如何用解数学题的方式化解焦虑、体育组的马老师教大家简单的放松操、语文组的吴老师给大家演示大笑疗愈法……朱老师看到在人群中的王老师,他认真地听着学着,紧锁的眉头渐渐放松。
春天快结束时,学校举办“心理健康周”。令朱老师意外的是,李明报名参加了心理剧表演。舞台上,他扮演一个被考试压垮的学生,当演到崩溃大哭时,台下响起一片抽泣声。谢幕时,李明突然脱稿:“我以前觉得求助是软弱,现在明白了,承认需要帮助才是勇气。”
五月的雨来得突然。放学时分,朱老师看见校门口有个熟悉的身影在徘徊。是上学期辍学的李晓雨,她撑着一把破旧的伞,裤脚全湿透了。
“我想……继续咨询可以吗?”李晓雨的声音比雨声还轻。她手腕上隐约可见几道白痕,像未愈合的伤口。
咨询室里,雨点敲打着窗户。李晓雨说她在饭店打工时,经常偷偷看心理学书籍。“有一次,一个醉酒的大叔在店里哭,我……我给他倒了杯热水。”她的眼睛突然亮起来,“他后来专门来道谢,说那晚他本来想……”
朱老师想起社区心理服务中心的志愿者培训通知。第二天,李晓雨的资料表上多了一个红勾。暑假里,朱老师去社区中心讲座时,看见李晓雨正在教老人们做手指操,她的手腕上戴着一串彩色编织手链。
教师节那天,朱老师收到李明从大学寄来的明信片,背面画着一座小桥。办公室的门被敲响,校长带着几个陌生面孔走进来:“朱老师,这几位是来学习我们心理健康教育经验的。”
窗外,今年的泡桐花早已谢了,但朱老师似乎又闻到了那股淡淡的香气,她一直记得泡桐花的花语“永恒的守候”,这株百年泡桐树一直守候在校园里,而她立志像泡桐树一样,一直守护孩子们的心理健康。
看着从泡桐树下走过的一群学生,他们有说有笑的,她想起十年前老校长的话,忽然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心桥从来都不是单向的。每一个走过的人,都成了桥的一部分。
又是一个傍晚,朱老师去社区给志愿者讲授心理健康课时,看见门前的公告栏上贴了一则通知,上面写着:“周日下午三点,社区心理互助小组——‘心桥’,欢迎您的到来!”朱老师看到活动的联系人是李晓雨。
夕阳把白纸染成了温暖的橘黄色,朱老师的眼睛不知怎么竟湿润了……

 四川法制网
四川法制网
 法治文化研究会
法治文化研究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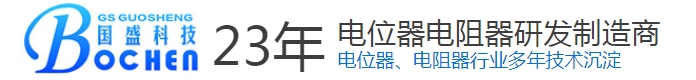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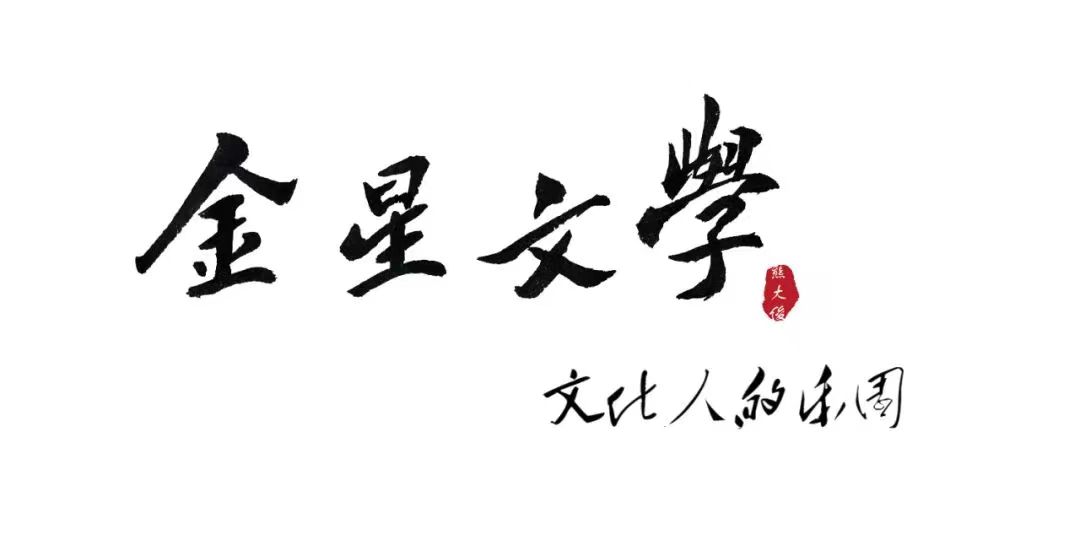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10402001487号
川公网安备 5101040200148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