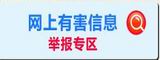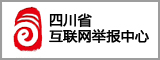“苎”,坦白说,这个字在我念初中时还不认识。直到1978年隆昌从宜宾地区划归内江地区后,才知道隆昌所产“苎麻”的“苎”便是这个字,读zhù,而非我臆想中的读“竹”(zhú)。
隆昌地处内江市东南端,现为内江市代管的县级市。不久前赴隆昌,自然是观石牌坊、游古宇湖。午后阳光洒落,路边几株植物映入眼帘:叶片呈锯齿状,叶面与茎秆覆有细绒。同行朋友说,这便是苎麻,可用来织“夏布”。我轻轻“哦”了一声,其实我对它的了解比她略多些。
“苎麻”这个散发着古老气息的词语,让人不禁联想到《诗经》里描绘的美丽姑娘在河边洗“纻”(即如今的苎麻);三星堆遗址4号坑考古出土的苎麻线,印证了蜀人当年已身着麻布衣裳;杜甫《夔州歌十绝句》中“蜀麻吴盐自古通”提及的亦是苎麻;更可遥想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描摹的“腰机”吱呀声,以及明清商队驮着成捆夏布行走川南古道,马蹄在青石板上踏出火星的场景。这些古老记忆藏在苎麻细弱的秆茎纤维里,伴着叶面的细小绒毛在季风中飘荡千年,化作肌理各异的夏布。
为何称作“夏布”?一说织布工艺源自夏朝,一说与“华夏”相关,还有说因夏季穿着透气凉爽,故名“夏布”。
听隆昌人讲,从一株苎麻到制成夏布,需历经十几道工序。首道工序便是剥离麻皮与麻秆间的纤维层,将麻纤维漂白后撕片成缕,梳成细丝。长而强韧的苎麻纤维逐根捻接,使麻丝由短变长,“绩”后的线卷成茧状纱团。再经洗浸、绩纱、织布等工序,终成夏布,恰似化茧成蝶。
苎麻一年可收三季,俗称“头麻”“二麻”“三麻”。头麻于谷雨时节萌发,晨光中一片新绿,是整季麻中产量最大的。蝉鸣最盛时,二麻在7月骄阳下生长。我们赴隆昌时,正值“二麻”长势旺盛。初秋之后,三麻染上渐浓的霜色。天再寒,叶落后的茎秆可砍作柴烧,腐烂的落叶秸秆化作土壤有机质。这看似不起眼的植物,从叶到根无一处浪费,连种子都具有药用价值。
苎麻种植与夏布生产在隆昌已有上千年历史,隆昌素享“夏布之乡”的美誉。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移民带来湖广麻布生产经验,与隆昌本地技术融合,历经数代改良,形成一套独具匠心的工艺流程。以优质苎麻为原料手工编织的“隆昌麻布”,因光滑平整、配纱适宜、梭数均匀、莹洁润泽、坚韧耐用等特点,蜚声中外。
在夏布上作画始于内江职业技术学院王少农教授。他发明的中国书画夏布使中国画可长久保存,获国家原创性科技发明专利。王少农被文化和旅游部评为“影响中国的100位艺术大家”“国务院国礼特供艺术家”,其首创的七大类艺术品被列为四川省旅游特色商品品牌和优秀旅游商品品牌。他著有《中国夏布画创始人王少农作品精选集》《中国夏布绘画艺术》(荣宝斋出版)、《中国夏布画创始人王少农作品选》(世博会邮票珍藏版,国家邮政局审批、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中国艺术三人行》(与刘大为、张海合著,荣宝斋出版)。其作品《荔枝图》入选人教版新教材高中语文一年级下册、九年制义务教育八年级下册和《100幅中国名画》。
近年来,为保护夏布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江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中国夏布研究所,利用夏布肌理创作中国画,拓展了除绢、纸以外的作画材料,为传统手工艺注入新内涵,开拓了市场前景。王少农教授对夏布画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以夏布为载体的画作具有质感好、着色佳、视觉美,不易损坏、变质,可长久保存等特点;其天然独特的肌理纹路构成原创作品的唯一性,形成天然防伪标志,保障了作品的真实性与不可复制性。
夕阳西下,我们一行即将返回内江,忍不住再次回望路旁锯齿状叶片的苎麻。那锯齿宛如大地的绿色针脚。上了年纪的乡农说,苎麻又称“中国草”——在棉花传入中国前,它是古代最重要的纤维作物之一,历史比丝绸更悠久,无论贵族平民皆可穿用。如今,夏布成为现代人“穿在身上的自然”象征,手工织布更成为年轻人新奇的“国风”体验。夏布的应用场景日益广泛,除制衣帽外,还融入家居领域:灯罩、茶几、隔帘、窗帘……布面经纬化作充满呼吸感的肌理,以“静、慢、韧”之气安抚快节奏生活中的浮躁。譬如我身上这件藏蓝短袖衫,采用苎麻面料,已购置七八年,多次洗涤后,蓝色仍透着植物浸染的静谧与清凉。
为体验郊游野趣,我们特意选了一条小路。车窗外,夕晖掠过片片苎麻地,仿佛有古老歌谣在叶片间颤动。更远处,田地阡陌纵横,金鹅江漫过鹅卵石滩,浸润两岸赭红土地。江上鹭影掠过——这条江宛如一匹流动的夏布,苎麻的气息在水波中生生不息地漂洗、舒展。
巧的是,回到内江在五星湿地公园漫步时,竟看到几株野生苎麻。风起时,叶片翻转,发出窸窸窣窣的清脆声响,继而反弹,似琵琶声嘈嘈切切……

 四川法制网
四川法制网
 法治文化研究会
法治文化研究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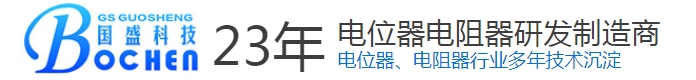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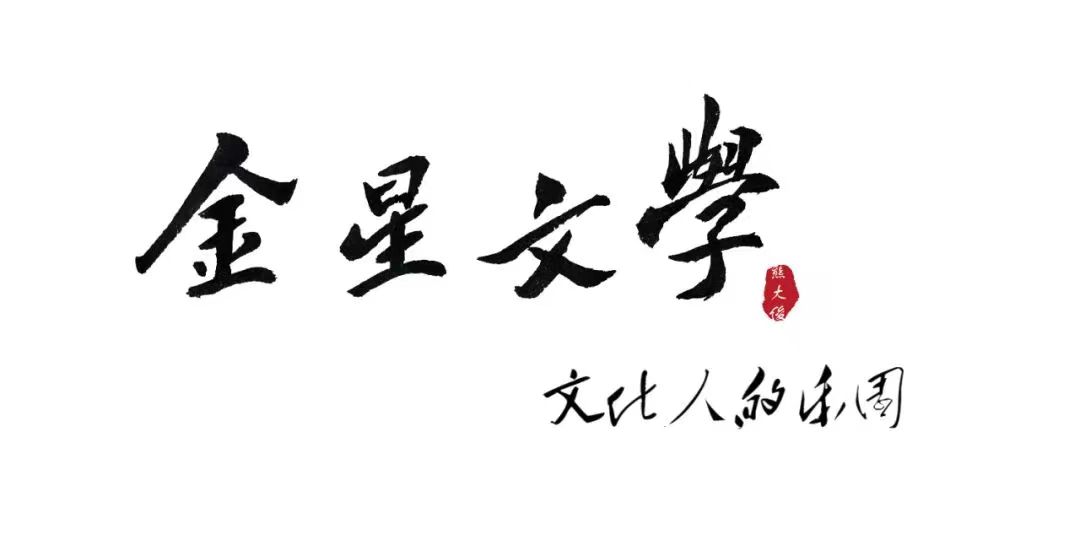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10402001487号
川公网安备 51010402001487号